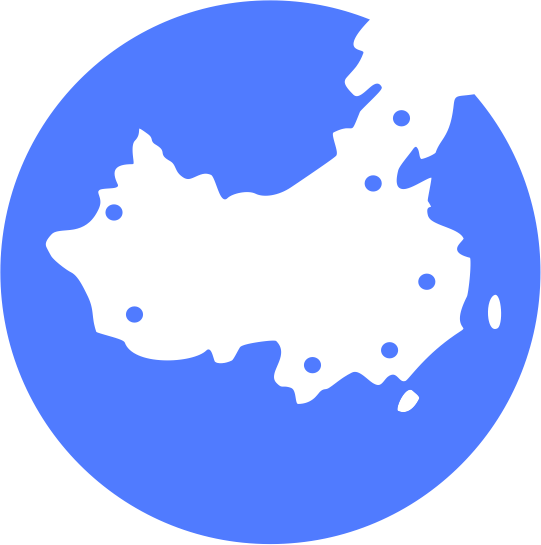「通過公元554年查士丁尼的帝國復興,天主教會使帝國復甦!此後,該教會引導了帝國隨後的所有復興。」——傑拉爾德·弗盧里
到五世紀末,羅馬帝國看似已死。它失去了北非、中東和西歐的大部分領土。首都羅馬在公元476年被哥特人洗劫。帝國經濟陷入崩潰,領導層被摧毀,且由外族人指揮。
破壞來自北方和東方的蠻族部落。在五世紀期間,羅馬先後由三個不同的日耳曼部落統治。這些部落不僅摧毀了羅馬的世俗領導層,還推翻了羅馬主教及其宗教。
儘管失去了權力和威望,羅馬天主教會——及其成為統治世界帝國的普世宗教的野心——並未消亡。這種宗教及其志向在一個地方尤其保持生機:君士坦丁堡。
但天主教會如何重返歐洲之巔呢?
公元527年,一位強大而雄心勃勃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登場,這是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的首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自認為是羅馬凱撒。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清除西部領土的日耳曼部落,重新征服羅馬,並統一羅馬帝國的東西部。他的座右銘概括了一切:「一個帝國,一個教會,一個法律。」
他也身體力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前羅馬帝國成為他的國家,羅馬憲法成為他的法律,羅馬天主教成為他的宗教。那些阻礙他或反對他的人被迅速、痛苦地消滅——數以千計。
恢復天主教
查士丁尼的帝國願景比過去兩百年的任何統治者都要宏大。「比起自君士坦丁以來的任何皇帝,他更相信自己肩負著救贖世界的使命,」湯姆·霍蘭在其暢銷書《劍影之下》中寫道。他是「羅馬歷史上最具力量、活力和自我中心的皇帝之一。」
天主教當局說服查士丁尼,要贏得戰鬥並恢復帝國,他需要上帝的支持。他們說,通向上帝之心的道路是清除帝國中的異教和異端。「幫我摧毀異端,我將幫你摧毀波斯人,」君士坦丁堡主教內斯托里烏斯對查士丁尼的一位前任說道。
查士丁尼遵從並立即開始清除國內所有非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根據皇帝的命令,法律規定:「我們命令所有遵循此法律的人採用天主教基督徒的名義,視其他人為瘋狂和精神錯亂,我們命令他們承擔異端之恥;待他們應得的神聖報應平息後,根據我們從天皇判斷中獲得的憤怒,他們將受到進一步懲罰……」(重點強調)。
在查士丁尼治下,一個人要麼是天主教徒,要麼是異教徒。法律被制定來摧毀異教徒。其中一條法律規定:「不接受這些教義的人不得將真宗教之名用於他們的欺騙信仰;他們應被公開罪行烙印,並被逐出所有教堂門檻,完全排除在外,我們禁止所有異端在城市內舉行非法集會。然而,若有任何叛亂行動企圖,我們命令以無情的暴力將他們驅逐出城牆外,並指示全世界所有天主教教堂應由接受尼西亞信經的正統主教控制。」
擁有基督徒奴隸的猶太人被處死。查士丁尼和天主教會一起禁止所有非基督教的崇拜場所,包括遠至北非的猶太會堂。猶太人被禁止慶祝逾越節。「沒有哪位前任君主如此關注教會事務,也沒有哪位像他這樣積極迫害異教徒和異端,」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書》寫道。查士丁尼「以更嚴格的法律更新了對這兩類人的限制。」
與查士丁尼同時代的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在其《秘史》中寫道:「在整個羅馬帝國的基督徒中,許多人持有被正統教會稱為異端的不同教義:如蒙塔尼派、薩巴提派,以及其他使人心偏離正道的教義。查士丁尼命令所有這些信仰被廢除,代之以正統教義:對於不服從者,懲罰包括剝奪異端將財產遺囑給子女或其他親屬的權利……特工被派往各地,強迫他們遇到的任何人放棄父輩的信仰……因此許多人在迫害派的屠刀下喪生……。」
查士丁尼的迫害如此徹底,以至於一些人被逼自殺。普羅科皮烏斯寫道:「居住在弗里吉亞的蒙塔尼派將自己關在教堂內,點燃教堂,葬身火海,升向榮耀。」在這種教會與國家的聯盟下,「整個羅馬帝國成為屠殺和逃亡的場景。」
普羅科皮烏斯寫道:「在查士丁尼看來,殺戮若針對不與他同信仰的人,幾乎不應算作謀殺。」查士丁尼將對異端的迫害提升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君士坦丁時期,異端被流放,有些被殺害。在查士丁尼治下,他們被成千上萬地屠殺。
恢復教皇權威
清除異教徒和異端的共同追求幫助正式確立了始於君士坦丁的教會與國家合作關係。「教會與國家的整合過程,由君士坦丁開始,一直持續到兩者密不可分,」保羅·約翰遜在《基督教史》中寫道。「拜占庭帝國實際上成為一種神權政治形式,皇帝執行祭司和半神聖職能,正統教會則成為負責精神事務的國家部門。」
皇帝查士丁尼還恢復了羅馬天主教會的領導權,包括教皇的至高權威。查士丁尼教會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從一開始就是與羅馬教皇建立密切聯盟,儘管羅馬被哥特人征服,教皇仍被廣泛認為是教會的領袖。
查士丁尼知道,要恢復羅馬帝國,他需要羅馬主教的認可。在給教皇的一封信中,查士丁尼稱他為「所有聖潔教堂之首」。在查士丁尼的一部小說中,他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最神聖座位,新羅馬,在古老羅馬最神聖使徒座位之後排名第二」(亞歷山大·瓦西里耶夫,《拜占庭帝國史》)。
羅馬主教繼承了羅馬帝國的學者和學術。保羅·約翰遜解釋說:「羅馬主教擁有準確且權威的聖人名單、科學的日期和日曆系統,以及涉及教會教義、實踐和紀律的所有問題的參考系統,這在與西方各地主教區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優勢;他們越來越依賴羅馬,不僅因為他們崇敬聖彼得及其聖殿,還因為羅馬知道答案。」
查士丁尼是東方的皇帝,但最終的宗教權威居住在羅馬的七座山上!
法律中的宗教
天主教對查士丁尼帝國的影響遠遠超出宗教。皇帝恢復天主教為國教後,他與教會共同制定了國家的法律。
「在四世紀期間,教會越來越參與法律制定過程,」約翰遜寫道。「五世紀中葉的第一部偉大法律彙編《狄奧多西法典》的許多內容是由教會制定的。當然,世俗法與教會法之間沒有區別;在管理和傳播其中之一時,教會自動使另一個為人所知。」
在公元529年至534年間,查士丁尼為他復興的羅馬帝國頒布了國家憲法。這份總括性文件被稱為《民法大全》,也稱為《查士丁尼法典》。它基於羅馬的法律,這些法律大多由天主教會撰寫。這一新的法律標準將羅馬天主教提升到國教地位,並禁止任何其他宗教活動和集會。
它還將教皇與皇帝之間的戰略關係納入法律框架。教皇宣稱皇帝是羅馬帝國的唯一真正統治者,而皇帝則保護羅馬天主教免受所有外部威脅。
這套羅馬法律成為查士丁尼帝國的法律基石——以及隨後所有神聖羅馬復興的基石。
即使在今天,歐洲的法律和司法仍植根於《查士丁尼法典》。俄亥俄州律師卡里·R·阿爾本在《美國律師協會雜誌》中寫道:「兩千多年來,羅馬法一直引導著文明國家和世界上許多野蠻民族的命運。」他總結查士丁尼的工作說:「查士丁尼的這部彙編鞏固了他之前一千年的羅馬法,並成為了全世界大多數後期法律法典的基礎。」
但請記住:皇帝查士丁尼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主教會建立的!
重新征服羅馬
天主教的影響滲透到查士丁尼政府的每個部分,甚至包括其外交政策。查士丁尼的法律強制在其領域內傳播天主教,但他也希望在國外傳播。「在羅馬歷史上,首次將異教國王的皈依作為國家優先事項,」湯姆·霍蘭寫道。
「當然,教會自成立以來一直渴望將十字架植入世界的遙遠角落,」霍蘭繼續說。「然而,羅馬國家有責任為這一使命做出貢獻,則是一個更激進的假設。」
在查士丁尼完成新憲法編纂的次年,他將目光投向重新征服前羅馬帝國的領土。既然他已將羅馬天主教定為帝國的官方宗教,確保該宗教的主要所在地羅馬成為其領域的一部分就顯得至關重要。
公元535年,統治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爆發內亂。皇帝查士丁尼決定利用這場動亂發起戰爭以統一帝國。在羅馬教皇提供政治支持下,查士丁尼派遣了一支軍隊及其最有天賦的將軍貝利薩留斯前往意大利南部。五年內,東哥特國王維提吉斯被俘,意大利大部分地區被征服。東哥特人又多次反撲。然而,最終,最後一位東哥特領袖的血衣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放在查士丁尼腳下,作為其死亡的顯著證據。
經過近二十年的戰爭,皇帝查士丁尼奪回了意大利、達爾馬提亞和西西里——並復興了羅馬帝國。
皇帝查士丁尼於公元554年通過一道名為《務實制裁》的詔令正式宣布這一帝國復興。該詔令將東哥特人從羅馬天主教會奪取的所有土地歸還給梵蒂岡控制。它還將教皇及其梵蒂岡階層在羅馬被蠻族入侵前享有的所有權利、權力和特權歸還。帝國的兩半現在統一了。歷史上首次,羅馬天主教會統治國家,而不是國家控制教會。哥特人造成的致命傷口癒合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第一次復興開始了(參見「致命的‘傷口’」,第188頁)。
進入山谷
查士丁尼復興的羅馬帝國短暫存在。在他去世後幾年,拜占庭對意大利的控制開始瓦解。倫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大陸,拜占庭人僅能控制沿海城市。意大利半島再次分裂。
儘管帝國復興結束,意大利大部分地區解體,但一個核心機構繼續延續其法律和生活方式。天主教,查士丁尼復興和前羅馬帝國的本質,依然生機勃勃。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從羅馬運作的天主教會在意大利和西歐保持了影響力。最重要的是,羅馬帝國的火焰在梵蒂岡以及教皇和天主教領袖的心中繼續燃燒。梵蒂岡耐心觀察和等待,知道復興羅馬帝國的機會終將到來。
從五世紀到七世紀,日耳曼部落控制了北歐和西歐——曾是西部帝國的領土。儘管這些部落拒絕羅馬政府,令人驚訝的是,許多部落皈依了羅馬的宗教。此外,西歐的政治權力真空給了羅馬教會一個機會,正如保羅·約翰遜所寫,創造一個「以其基督教形象」為基礎的社會。
隨著天主教在前帝國各地被接受,教會看到了施加影響的機會。西歐缺乏道德和政治權威及領導力,使天主教會成為唯一有組織、富有且複雜的機構。
保羅·約翰遜的以下陳述令人震驚。帝國復興崩潰後,許多城市倖存下來,「以天主教主教為主要居民和決策者,」約翰遜寫道。「他組織防禦,管理市場經濟,主持司法,與其他城市和統治者談判……在某些情況下,主教組織了對‘入侵者’的‘文明’抵抗。然而,更常見的是,他們與入侵者談判,並隨著時間推移成為他們的顧問。」
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羅馬天主教會承擔了制定和維護法律、培訓和教育歐洲未受教育者的責任。約翰遜繼續說:「作為異教社會,所有部落聯盟都擁有龐大而古老的慣例法體系,未被書寫但被記憶,並根據變化的需求緩慢且偶爾更改。當教會與這些蠻族社會接觸,誘導他們接受洗禮或在阿里安派的情況下與羅馬完全共融時,其主教幾乎立即建立了將基督教法律習俗與現有異教法律聯繫起來的安排。」
歐洲此時未由羅馬的中央政治政府統治,但仍在羅馬帝國的形狀和形式中被創造。由誰創造?由梵蒂岡和散佈在歐洲的數千名羅馬天主教主教。
約翰遜舉了倫巴第國王羅塔里的法律《羅塔里詔令》為例。這部法律不是用倫巴第語,而是用羅馬的語言拉丁語撰寫。一些材料直接從查士丁尼的法律中抄錄。「事實上,這部法典不僅包含羅馬元素,還以羅馬法為正式基礎,」他寫道。「羅塔里是阿里安派;但他的朝廷顯然已被天主教神職人員滲透,他的法典表明他的政治和法律思維在道德層面上顯然受到基督教影響。」
教會還負責編寫歷史。「如果說教會在蠻族心中與未來相關聯,它也確立了自己作為他們過去的監護者和解釋者的地位,」約翰遜繼續說。「教會從一開始就擁有編寫歷史的壟斷地位。這對其在黑暗時代社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至關重要。」
天主教神職人員記錄了部落的口頭傳統。在封建歐洲,天主教修士和神職人員是國王和領主的抄寫員,負責書寫和儲存重要記錄。人們越來越通過天主教會的視角看待自己國家的歷史。早期中世紀的歐洲人被教導將其部落皈依天主教視為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時刻。
教會將過去的學問和知識帶入後羅馬世界。修道院成為古代知識的儲存庫,並將其傳遞到中世紀歐洲。在沒有中央政治權力領導的情況下,教會壟斷了歐洲的文化和教育。「這為教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通過其根基捕獲社會。它不僅有機會建立對教育的控制,還能以基督教環境重新創造教育的整個過程、內容和目的,」約翰遜寫道。
這種教育的基礎由一位強大的天主教主教伊西多爾設計。約翰遜寫道,這成為「西方約800年所有教學的基礎。」伊西多爾的作品「決定了教育方法以及從小學到大學層次的內容。此後所教的一切不過是他所寫的闡述:中世紀的思維無法突破他的體系。」他的工作基於古代世界的基礎,並通過天主教會將這些思想傳遞到現代世界。
今天,我們認為可以自由地在書籍、互聯網、大學中獲取知識是理所當然的。在中世紀歐洲,正規教育很少見;甚至書籍也極其稀缺。大多數人不會讀寫。世俗和宗教知識的主要儲存庫是天主教神父和當地修道院。
教會還從羅馬的廢墟中承載了實用知識。作為羅馬領先家族的後裔,主教們是熟練的土地所有者和地產管理專家。「在蠻族眼中,教會人士是‘現代’農民,他們記賬、提前計劃、投資,」約翰遜寫道。「主教區和修道院共同構成了歐洲農業經濟的核心。主教和修道院長是社會的創新精英。」
修士們「在沒有人能拯救農業時拯救了它,」馬薩諸塞農業學院院長亨利·古德爾說。來自《古代與現代教會史研究所》的約翰·洛倫茨·馮·莫斯海姆說:「他們到哪裡,就將荒野變成耕地:他們從事養牛和農業,親手勞動,排乾沼澤,清除森林……通過他們,德國被耕種並成為一個富饒的國家。」
確實,天主教會對歐洲歷史的影響遠比大多數人所知的廣泛。今天我們低估了——甚至到最小的細節——歐洲是由天主教會建立的程度!
尋找另一位英雄
儘管在六世紀到八世紀,天主教當局擁有相當大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影響力,但他們知道,要獲得普世霸權,他們需要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幫助。梵蒂岡需要另一個查士丁尼,另一個它可以激勵和引導的強大人物,進行另一場統一歐洲並復興古羅馬帝國的十字軍東征。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七世紀首先開始創造這位英雄。約翰遜這樣描述格里高利的努力:「他認為未來在於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新興國家’。羅馬主教的任務是將他們引入基督教,將他們與教會系統整合。哀嘆帝國毫無用處。‘老鷹,’他寫道,‘已經禿了,失去了羽毛……參議院在哪裡,羅馬的老人們在哪裡?都沒了。’……格里高利宣揚一種基本的福音宗教,剝離了古典的複雜性和優雅;他派他的修士將其傳授給野蠻、粗魯、講日耳曼語、留長髮、擁有未來強大力量的戰士。」
教皇格里高利開啟了與「阿爾卑斯山以北新興國家」的聯盟,這一聯盟在接下來的一千年中斷斷續續地凝聚。到八世紀中葉,隨著北歐的日耳曼部落現在接受天主教,梵蒂岡已準備好利用那位將復興羅馬帝國並永遠被視為歐洲統一之父的人。
天主教日曆
天主教對全球影響的一個顯著衡量是其對時間定義和測量的控制。即使在今天,雖然天主教的存在似乎不如過去那樣無處不在,我們仍然生活在由古老教皇創建的日曆中:格里高利日曆——以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命名。該日曆圍繞著將復活節的日期與春分對齊,確保天主教的異教節日相對於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落在正確的時間。
這個日曆基於儒略日曆,這是公元前45年由尤利烏斯·凱撒確立的羅馬日曆。他選擇了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月份名稱和長度(除了七月和八月,分別以尤利烏斯和奧古斯都命名)。但儒略日曆後來被梵蒂岡修改。
令人震驚的是:上帝實際上預言了天主教會將改變時間本身!
閱讀但以理書7:24-25的預言。這裡上帝談到「小角」,即天主教會。(這在第九章中有詳細證明。)「他將說大話反對至高者,折磨至高者的聖徒,並打算改變時間和法律:他們將被交到他手中,直到一時、兩時和半時。」
天主教會改變人類測量時間方式的動機是什麼?第25節的上半部分給出了答案:這是試圖通過從人類記憶中移除對上帝真正聖日和安息日的知識來摧毀它。
深入思考赫伯特·W·阿姆斯特朗在《異教節日——還是上帝的聖日——哪個?》中的以下引述:
在自羅馬陷落至今統治西方世界的這十個王國中,出現了另一個「小角」,其「樣子比他的同伴更強大」。換句話說,另一個政府,實際上更小,但卻支配所有其他政府。研究預言的學生認識到這個「小角」是一個偉大的宗教階層。在這一預言的第25節中,說這個階層將「打算改變時間和法律」。
這同一個權力在啟示錄第17章中再次被提及,這裡被描繪為統治地球上的國王和王國,迫害真正的聖徒。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這個權力改變了時間!
上帝從日落開始計算日子,但「小角」將其改變,現在世界在半夜以人造的手錶開始一天。
上帝以真安息日,即一周的第七天結束來開始一周,但世界在半夜,即一周的第二天,開始工作周。
上帝以新月開始月份,但這個「小角」誘導世界根據笨拙的異教起源的人造日曆開始月份。
上帝在早春開始一年,當自然界萬物萌芽時,但古異教羅馬使世界在死冬中開始一年。
上帝給祂的子民一個真正的休息日,旨在讓他們持續記住並真正敬拜真神——一個記念上帝創造的日子——一周的第七天。但「小角」強加給一個受迷惑的世界,遵守異教徒崇拜太陽的日子,即一周的第一天,稱為星期日。